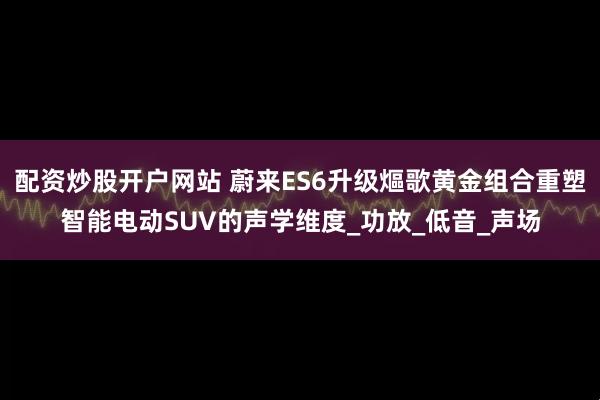“爹,今天您五十大寿,咱们去拍个合影吧。”1919年11月13日,长沙城北的木板房里弥漫着腊肉的香味,毛泽东端着热茶走到父亲面前。毛贻昌拿起粗瓷茶碗实盘配资网站,手指摩挲着温热的表面,目光扫过桌上特意准备的家乡菜肴,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酸涩。自从文七妹去世后,家里再也没有了这样的烟火气,仿佛一切都沉寂了。
照相馆的布景是典型的江南院落,青砖灰瓦,四周被精心布置的花木围绕。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,毛贻昌挺拔的身躯微微颤动。这个在韶山冲经营着二十多亩土地的家主,今天却显得有些不自在。他特意换上了洗得发硬的青布长衫,袖口的毛边被岁月磨出痕迹,丝毫无法掩盖那种因多年持家所积累的风霜与劳苦。谁曾想,这张泛黄的老照片,竟成为了父子俩定格的瞬间。
回溯五十年,1870年的韶山冲依然在饥荒的阴影下艰难度日。毛家老宅的土墙破旧不堪,七岁的毛贻昌蹲在灶前,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把最后的半碗糙米倒入滚烫的铁锅。作为家里的长子,十岁时他便开始跟随父亲到田里劳作,十七岁时,家里的经济困境迫使他接过了家主的重担,那时,他们已经背上了八石稻谷的外债。每逢春荒,他便记得自己曾啃过树皮,那个记忆像烙印一般深深刻进了他年轻的骨骼中,久久无法抹去。
1893年的一个寒冷夜晚,二十三岁的毛贻昌静静地收拾着包袱。月光透过茅草屋顶的破洞洒在熟睡的妻子和襁褓中的润之身上,他最后一次回望躺在土炕上的家人,咬着牙将绑腿扎紧。与其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支撑,不如走出这片困境,去湘军大营找一条活路。军营的号角声吹散了文七妹的哭泣,却没能吹走毛贻昌衣袋里紧紧握着的全家福。那是一幅他离开家时请画匠画的全家合影,画中的父母和弟妹的面容早已模糊,唯剩一团模糊的影像。
展开剩余69%在长沙城驻防的五年间,毛贻昌的军饷从每月三两涨到了五两。与那些同袍们每月拿着饷银直奔酒馆和赌坊不同,这个精明的湘潭汉子却总是在营房的角落里默默打着算盘。他把银钱托人带回韶山冲,先是清偿了家族欠下的债务,然后又购买了两亩水浇田。待他最终解甲归田时,毛家已经拥有了十五亩良田,两头壮牛,成为韶山冲中为数不多的殷实户人家。
有趣的是,这位从零开始、白手起家的农夫对土地的执着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。有一年秋收之后,堂弟毛福生家遭遇火灾,毛贻昌连夜带着钱袋上门,直言:“福伢子,你家南坡的那三亩田,我按市价加两成。”当堂弟含泪在契约上按下手印时,十七岁的毛泽东忍不住砸了算盘:“爹这是趁火打劫!”毛贻昌拿着旱烟杆,重重敲在桌角上:“崽啊,这世道比田埂还难走,心软就要饿肚皮!”
191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毛家老宅的门轴吱呀作响。十七岁的毛泽东背着蓝布包袱,袖口里揣着父亲塞给的六块银元。毛贻昌站在门框旁,看着儿子渐行渐远,突然高声喊道:“润之!在外头可别省了饭钱!”多年后,毛泽东回忆起这个场景时,他说道:“父亲喊话的瞬间,山雀扑棱棱地飞过,遮住了他眼中的水光。”那是一个既温暖又痛苦的告别。
命运似乎总爱在人们的生命中开些残酷的玩笑。1919年深秋,毛泽东正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,突然接到家书,母亲病重的消息让他匆忙南下。当他风尘仆仆赶回韶山冲时,只见堂屋内停着一具漆黑的棺木。跪在母亲灵前的毛贻昌,仿佛突然苍老了十岁,这个一直刚强的老汉,背微微佝偻,手指紧紧掐进棺木的缝隙,仿佛想要将亡妻从黄泉路上拉回来。
“爹,跟我去长沙住些时日吧。”在守孝期满之后,毛泽东几乎是恳求般地望着父亲。在长沙潮宗街56号的租屋里,他笨拙地模仿母亲生前的做法,亲手为父亲煨莲子猪肚汤。在11月的寿宴上,毛贻昌抿着儿子敬上的米酒,忽然提起往事:“那年你娘怀你的时候,梦见南山飞来一条金龙……”话未说完,他的声音便哽住了,混合着酒水的泪珠滴落在粗瓷碗里。
三个月后,照相馆的镁光灯已经褪去,北京法部胡同的邮差带来加急电报。当时,毛泽东正在筹备湖南改造促成会,他看着“父病故速归”这五个字,毛笔从手中滑落,墨汁洇在宣纸上,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墨迹。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:“当我赶回家时,灵堂已经设好了,连说最后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”韶山冲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,那个戴眼镜的教书先生跪在父亲的坟前,把那张父子合影的照片埋进黄土,又从怀里掏出一本《新青年》,焚作纸钱。
毛贻昌不曾知道,他教给儿子的算盘,最终成了衡量中国农村的标准;他逼着儿子背的《曾文正公家书》成了延安窑洞里批注最密的书;就连他那句“心软饿肚皮”的教诲实盘配资网站,也成了土改运动中的那句“矫枉必须过正”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华林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